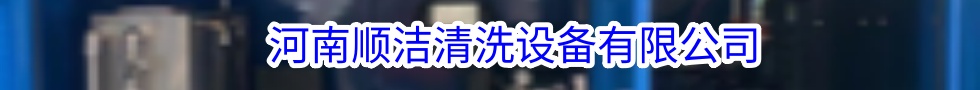自那日起,她常常做梦。
或梦见与那人隐居山林,却又因故分离,或梦见与那人初成眷属,却又因战独守。
每一个片段都极乱,以至于她清晰记得的,只剩下昨晚梦见的那个了。
她该是一名中阶官员家的独女,而他是将军家里的长子。
他有个胞弟,生的与他极像,又另有一门高官亲戚,二品大官的家里有个尚才及笄的女儿。
算起来,那女儿该算他的表妹。
她与他恋了数年,她从个未及笄的姑娘到了几近双十的年华,他从个尚懂情事的小郎到了年至弱冠的年龄。
六年不短,人生尚不过十几来个六年,况除去十几年的懵懂,姑娘家的年华确只剩堪堪十载。
她尚未嫁,他尚未娶,虽称不上完完全全的门当户对,却也差不离谱。况两家儿女又两情相悦,怎也不好拆了这对鸳鸯。
偏偏许下婚约不久,国与南夷开战。蓝眼褐发、体魄强健的南夷子们,一个可敌两个中原人。战事胶着,将军家的儿子又怎么能在此时办了婚事?
他被派去同父亲一起对抗南夷,她在家里等他,等他回来完那未完的婚约。
一等三年,所幸他平安归来,且立下赫赫战功。功名已敌其父。朝廷欲许其官位,却迟迟未下皇诏。那二品大官来寻他,道他若肯娶了他家女儿,此官位定然唾手可得。
他迟疑了。到底是铁血男儿,谁不愿功名显赫,位立高官?
只是...九年不短。
她已为他耗尽此生最美的时光,自己又怎能弃之于不顾?
他回绝了,虽有犹疑。
那善察言观色的大官却看出了他的犹疑。
自己的女儿自幼喜欢他得紧,只可惜他早早许了心意...况现下多一位将军之子做女婿,也实在是一门好婚事。
他的迟疑,终于是带来了一场逼婚。
朝廷之内关于他的流言一夜四起。道他在军帐之中饮酒作乐,道他与俘虏来的南夷美女寻欢...一切不好的传言都渐渐蔓延开来,连带着老将军也被冠上了教子无方的名号。
可怜老将军一生在外征战,空有一身铮铮铁骨,却不知朝廷上的尔虞我诈,他又尚进朝廷,不知如何应对。
他读遍兵法,却唯独不知朝廷上的三十六计。
他允了亲事,或许是迫于无奈,或许在他迟疑的那刻,他就弃了她的一片真心,也说不定。
纵然如此,他却对她说:“等我,三年之内,我定归家。”
她开始等他第四个三年。
那二品大官或是为了断绝后患,说服帝子将他派往一处驻守。
她失了他的消息,只得日日去将军府里,问他的胞弟誉。
誉总会细细告诉她他的近况,细细为她读他的来信。
他也会给她写信,且写的很多。她也知道他过的不好,却无能为力。
她自己又何尝过得好过。
她已经是二十几的姑娘了。
家中有父母的催促,她是独女,她得为家族绵延后代。
终于在第一年的末,她告诉誉,她想要放弃了。
她没有时间,也没了勇气,尽管她舍不得。
她再没有一个三年来挥霍,她已将至二十五,再美的模样也将老去。
誉却来求她,一个七尺男儿说得声泪俱下,誉告诉她,第三年,他一定、一定会回来。
她心疼了,答应等下去。
便是这样一拖再拖,这样到了第三年的末。
他终归是没有敌过那老奸巨猾的大官,只得身骑一马,舍了所有的行李,独自夜行赶回京城见她。
为了完他未完的婚约。
只可惜,她忘了结局如何。或许是见着了,或许是没见到。
因为她醒了,温暖的被褥提醒着她一切只是场梦。
尽管眼角温热的泪光如此真实。
该是见着了吧,或者说,但愿如此。
或梦见与那人隐居山林,却又因故分离,或梦见与那人初成眷属,却又因战独守。
每一个片段都极乱,以至于她清晰记得的,只剩下昨晚梦见的那个了。
她该是一名中阶官员家的独女,而他是将军家里的长子。
他有个胞弟,生的与他极像,又另有一门高官亲戚,二品大官的家里有个尚才及笄的女儿。
算起来,那女儿该算他的表妹。
她与他恋了数年,她从个未及笄的姑娘到了几近双十的年华,他从个尚懂情事的小郎到了年至弱冠的年龄。
六年不短,人生尚不过十几来个六年,况除去十几年的懵懂,姑娘家的年华确只剩堪堪十载。
她尚未嫁,他尚未娶,虽称不上完完全全的门当户对,却也差不离谱。况两家儿女又两情相悦,怎也不好拆了这对鸳鸯。
偏偏许下婚约不久,国与南夷开战。蓝眼褐发、体魄强健的南夷子们,一个可敌两个中原人。战事胶着,将军家的儿子又怎么能在此时办了婚事?
他被派去同父亲一起对抗南夷,她在家里等他,等他回来完那未完的婚约。
一等三年,所幸他平安归来,且立下赫赫战功。功名已敌其父。朝廷欲许其官位,却迟迟未下皇诏。那二品大官来寻他,道他若肯娶了他家女儿,此官位定然唾手可得。
他迟疑了。到底是铁血男儿,谁不愿功名显赫,位立高官?
只是...九年不短。
她已为他耗尽此生最美的时光,自己又怎能弃之于不顾?
他回绝了,虽有犹疑。
那善察言观色的大官却看出了他的犹疑。
自己的女儿自幼喜欢他得紧,只可惜他早早许了心意...况现下多一位将军之子做女婿,也实在是一门好婚事。
他的迟疑,终于是带来了一场逼婚。
朝廷之内关于他的流言一夜四起。道他在军帐之中饮酒作乐,道他与俘虏来的南夷美女寻欢...一切不好的传言都渐渐蔓延开来,连带着老将军也被冠上了教子无方的名号。
可怜老将军一生在外征战,空有一身铮铮铁骨,却不知朝廷上的尔虞我诈,他又尚进朝廷,不知如何应对。
他读遍兵法,却唯独不知朝廷上的三十六计。
他允了亲事,或许是迫于无奈,或许在他迟疑的那刻,他就弃了她的一片真心,也说不定。
纵然如此,他却对她说:“等我,三年之内,我定归家。”
她开始等他第四个三年。
那二品大官或是为了断绝后患,说服帝子将他派往一处驻守。
她失了他的消息,只得日日去将军府里,问他的胞弟誉。
誉总会细细告诉她他的近况,细细为她读他的来信。
他也会给她写信,且写的很多。她也知道他过的不好,却无能为力。
她自己又何尝过得好过。
她已经是二十几的姑娘了。
家中有父母的催促,她是独女,她得为家族绵延后代。
终于在第一年的末,她告诉誉,她想要放弃了。
她没有时间,也没了勇气,尽管她舍不得。
她再没有一个三年来挥霍,她已将至二十五,再美的模样也将老去。
誉却来求她,一个七尺男儿说得声泪俱下,誉告诉她,第三年,他一定、一定会回来。
她心疼了,答应等下去。
便是这样一拖再拖,这样到了第三年的末。
他终归是没有敌过那老奸巨猾的大官,只得身骑一马,舍了所有的行李,独自夜行赶回京城见她。
为了完他未完的婚约。
只可惜,她忘了结局如何。或许是见着了,或许是没见到。
因为她醒了,温暖的被褥提醒着她一切只是场梦。
尽管眼角温热的泪光如此真实。
该是见着了吧,或者说,但愿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