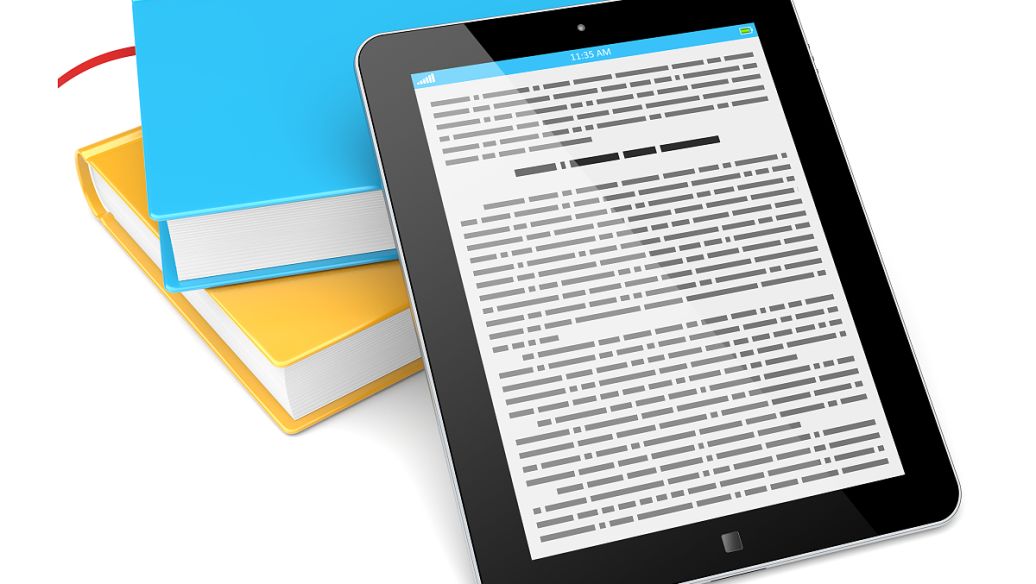到达位置后,杜宇萧梁两人跳下车,分头行动去了。
风间跳下车回头问秋云:“你在车里等我还是跟我一路。”
“跟你一路吧,反正没事做。”秋云掀开门帘走了出来。
风间扶着秋云的手,温软温软的,还没来得及更多的感受,她慢慢地下了马车,不动声色地将手又抽了回去。
两人走到一条偏僻的小巷口,眼前是一座废弃的掌心雷作坊。风间下车后,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味道,四周显得格外阴森。
“这就是被烧毁的作坊……”风间皱起眉头,向前走去。到处都是灰烬与残垣断壁。
作坊大门半掩,透出微弱的光线。风间用力推开大门,门板发出刺耳的吱呀声,眼前的景象让他心中一震。厂内的货架倾倒在地,满是黑色的焦炭,似乎延续着昔日的辉煌,但如今只剩下荒凉与凄凉。
“真是惨烈。”秋云在一旁轻声说,神情凝重。
她缓步走入作坊,目光细细打量着这片狼藉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
“风郎你看这是什么?”秋云将一枚令牌似的物件递给了风间。
风间接过物件,用衣袖擦去了上面的黑灰,露出了一朵莲花图案。
“长安城内似没见过有何人或者组织用过这般图案。”风间盯着图案瞧了一会没有任何思绪,只好将其收好,带回军营给将军查看。两人继续在这废墟之中找寻线索,也不知道有没有冤死在这里的百姓。
“风郎,你说要是有了冤枉事该怎么办?”秋云突然问。
“报官呗。”风间有些不解秋云的询问。
“若是那冤枉事是官做的又该如何?”
“这......”风间一时语塞。
风间突然想起了秋云的身世,她似乎是在说她自己,但这个问题非常要命,从情义上来说风间肯定是支持秋云的,他会说那就杀了那个狗官,但如今他是大唐的军曹参军,算是大唐的官,有些话不能乱说。
“小时候我其实挺难过的。”秋云轻声说。
风间心里微微一动:“为什么会难过?你家以前不是挺富有的吗?”
秋云愣了一下,找了一处干净的台阶,坐了下来仰望天井。
“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很累......我父亲是朝廷的大官。那时他公务繁忙,很少回来陪我和母亲,每次回来他都会考教我的学业,一旦背不上来那些诗词,他就会用戒尺打我手心。除了学业他还给我请了很多老师,有书画老师,有古琴老师,有舞蹈老师。”
“这么多老师啊?我老家在一个偏远的村里,想请一个识字先生都难。我小时候最喜欢下河摸鱼抓蟹,我娘怕我涨水被淹死,总是拿着柳枝条在河边等我上岸抽我。”
“我在学那些先生教的东西时,脑子里想的全是院墙外是什么样的世界。”秋云淡淡地说。
“后来呢?”
“有一次我被先生责罚打了手心,痛得我午睡时睡不着,我一个人悄悄跑出了院子。”秋云顿了顿,“那是我第一次逃离,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“那你还是蛮勇敢的。”风间夸奖道。
“表面上是,”秋云纠正道,“可真正逃离了那片院墙,我也不敢离家太远。在院墙里面时总是羡慕那群孩子,可以在外面嬉戏玩耍,可真正到了外面,我根本无处可去,陌生的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,路上的陌生人看我的眼神也都很奇怪。我就坐在离家不远的地方,一个人荡着秋千,摇着父亲给我买的拨浪鼓。”
“我小时候都没有玩具的。”
“我玩具还挺多的,都是我父亲给我买的。我把拨浪鼓想象成能实现愿望的法宝,只要我摇得够快,愿望就会实现,我就使劲地摇它,越摇越快,越摇越响......直到那两根绷着的线断裂,珠子崩到了我的额头上,痛得我哇哇大哭。”秋云声音低落,“其实我那时的愿望是想父亲回来陪陪我,可拨浪鼓坏了,我的愿望也就成真不了了。”
“还有呢?”风间觉得秋云还有很多话想说。
“府里的人发现我不见了,发了疯的到处找我。我就坐在秋千上,看着他们在街道上大声喊着我的名字,其实那个秋千离家很近的,只是没人相信,我跑出来就是在离家那么近的地方荡秋千,所以他们没有到那个地方找我。最后我觉得无聊了,主动走到了他们面前,他们一个个高兴得要哭出来。”
“那种情况我也会喜极而泣。”
“那天因为我失踪的消息传到了我父亲那里,父亲破天荒地放下事务,回到家见到了刚被找到的我,用戒尺狠狠打了我手心。”秋云说的专注,“父亲打我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哭,我笑了出来,我越笑就被打的越狠,于是我就边哭边笑,把父亲都逗笑了。我笑是因为我的愿望实现了。”
“你父亲其实对你还是蛮关心的。”风间说。
风间试着换成秋云的身份,从小接受各种教育,不能随便出去玩,不及格就会挨板子,一个人孤零零的,想着是有点悲伤。
“后来有一天,父亲被奸相杨国忠陷害,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。”
风间的心里忽然一空,呆呆地看着秋云。真是悲伤的氛围,凝结了周围的空气,让人压抑得不舒服。它想上去拥抱秋云安慰她,但他不敢,因为他看不见秋云的表情。
“父亲不在了,再也没有人让我读书练字学画弹琴跳舞了,再也没有人打我板子了。按理来说我应该要高兴的,所有的枷锁都没了,我自由了,没人能管我了。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,我的拨浪鼓坏了,我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。”
风间看见有一道晶莹的泪从秋云眼角流出。
“让风郎见笑了,”秋云不动声色地擦去那滴泪,“这些事情我从来没跟人说过。”
“没事的,”风间安慰道,“一切都过去了......”
“风郎你有没有什么愿望?”秋云问。
“赚大钱,当大官。”
“那要赚多少的钱才算够,当多大的官才算大?”秋云摇摇头,“人心的欲望总是越来越大,越来越难满足,不如说一个小点的愿望吧,最好能容易实现的,就像小孩柜子上的糖,站着够不到,垫垫脚就能摸到。”
“容易实现点的愿望?”风间抓抓头,“那就在乡下有一间房子和一块地吧。房子是最好能在靠近一条小溪的地方,每天种点地保证自己不被饿死,种完地搬一张藤椅躺在小溪边,吹着风,还可以钓鱼,阳光照在溪面上波光粼粼的,再喝杯自己酿的米酒就更满足了。”
“可是夏天在小溪边不会蚊虫太多吗?”
“这个倒是没考虑到。不过这样说的话也就春秋合适了,冬天寒风嗖嗖的,得冻出老寒腿。”
“这就是你想过的生活吗?”
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,老家有一个老头,他家就住在小溪边,他还有一根很长的钓鱼竿,无论什么季节,他都是躺在溪边钓鱼,他还会自己酿米酒,那米酒我趁他睡着喝过,一辈子忘不了那种感觉,美极了。有时候是真的羡慕那个老头。”
“你的性子有点懒散。”
“从小就是这样,能坐着从不站着,能躺着绝不坐着,但参军后就好了。”
“你小时候应该是那种总爱东想西想的小孩,一个人望着天,能看云的变化好久好久。”
喜欢东想西想......性子懒散......风间心里动了动,秋云似乎说对了他。
“我有时候也喜欢听风吹着树叶簌簌的响......”风间小声说。
“有机会的话,我也想过一下你的日子,躺在溪边,听风看云。”
杜预萧梁两人突然走了进来,似乎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。
“回去吧,明天有空再来,天黑了什么都找不到。”杜预说。
风间伸手将秋云拉起,她的手柔软而冰凉。
他凝视着她的眼睛,一如既往的漂亮,可上面似乎有一层雾,他读不懂她的内心。这一刻他离她很近,能清楚地闻到那些脂粉香气,却又相隔甚远。
他想到了秋云的话,你小时候是不是一个总爱东想西想的小孩,一个人看着天,能看云的变化好久好久。
他又想到了萧梁的话,算啦兄弟,这长安城有一百零八个坊市,就算每个坊市只有一个姑娘,你也有一百零八个姑娘,可以选一个去喜欢去爱。你这样纠缠下去,最终的结果就是像他们两人一样互相不得善终。
“我们走吧。”秋云放开了风间的手,很自然。
风间手上还残留着她的温度,此刻他们又远离了。
天已经黑了,街道两旁点着些许灯笼,马车载着四人走了,车轮好久没上过油了,一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风间把头搭在车窗看着窗外的街景,嘴里哼着清冷的调子。
风间走进将军的军营,把有着莲花图案的令牌放在他桌上。
将军拿着一封密信在看着什么,也不抬头看他:“有什么线索?”
“现场大部分东西都被烧毁了,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。”
将军看完密信再抬头看了眼桌上的东西,若有所思:“果然是白莲社。”
“白莲社是什么?”
“是一个邪教组织,这个你暂时管不着。东西放这,人滚吧。”
风间掀开门帘,正准备出去时回头:“将军,你有空的话还是休息一下吧,你的两个女人都很想你。”
“你要管我?”将军看着风间眼露寒光。
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风间一缩脖子,扭头一溜烟跑开了。
军营外的街道上,橘黄的灯笼挂在两侧,不时有寒风吹过,灯笼晃晃悠悠像麦田起伏的麦浪。
风间像一只迷途幽灵,跟着灯笼散发的光辉指引,一路走到了晋昌坊。坊门外有两只威武的石狮,专门阻挡各种邪祟入侵,一只石狮的阴影下靠着月玲单薄的身影。她快要睡着了,双手抱着蜷曲的双腿,靠着石狮的脑袋不时上下晃悠,一缕头发从耳根耷拉下来,在轻风中轻轻摇晃。
风间心里一动,这么晚了月玲在等着谁?还是她只是单纯的贪玩忘了回家。
风间走上前去,盯着月玲的侧脸瞧了会,有点脏脏的,他用衣袖擦去那些灰尘,那张小脸立刻显得娇嫩起来。
月玲缓缓睁开眼,看见面前之人后缓缓地无声地笑了,她伸出双手似乎要风间拥抱她,风间会错了意,伸出双手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说:“回家睡吧,地上冷。”
这时风间偏过头,听见远处的戏楼上隐约有歌声飘来:
“人生只似风前絮
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”
风间跳下车回头问秋云:“你在车里等我还是跟我一路。”
“跟你一路吧,反正没事做。”秋云掀开门帘走了出来。
风间扶着秋云的手,温软温软的,还没来得及更多的感受,她慢慢地下了马车,不动声色地将手又抽了回去。
两人走到一条偏僻的小巷口,眼前是一座废弃的掌心雷作坊。风间下车后,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味道,四周显得格外阴森。
“这就是被烧毁的作坊……”风间皱起眉头,向前走去。到处都是灰烬与残垣断壁。
作坊大门半掩,透出微弱的光线。风间用力推开大门,门板发出刺耳的吱呀声,眼前的景象让他心中一震。厂内的货架倾倒在地,满是黑色的焦炭,似乎延续着昔日的辉煌,但如今只剩下荒凉与凄凉。
“真是惨烈。”秋云在一旁轻声说,神情凝重。
她缓步走入作坊,目光细细打量着这片狼藉,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
“风郎你看这是什么?”秋云将一枚令牌似的物件递给了风间。
风间接过物件,用衣袖擦去了上面的黑灰,露出了一朵莲花图案。
“长安城内似没见过有何人或者组织用过这般图案。”风间盯着图案瞧了一会没有任何思绪,只好将其收好,带回军营给将军查看。两人继续在这废墟之中找寻线索,也不知道有没有冤死在这里的百姓。
“风郎,你说要是有了冤枉事该怎么办?”秋云突然问。
“报官呗。”风间有些不解秋云的询问。
“若是那冤枉事是官做的又该如何?”
“这......”风间一时语塞。
风间突然想起了秋云的身世,她似乎是在说她自己,但这个问题非常要命,从情义上来说风间肯定是支持秋云的,他会说那就杀了那个狗官,但如今他是大唐的军曹参军,算是大唐的官,有些话不能乱说。
“小时候我其实挺难过的。”秋云轻声说。
风间心里微微一动:“为什么会难过?你家以前不是挺富有的吗?”
秋云愣了一下,找了一处干净的台阶,坐了下来仰望天井。
“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很累......我父亲是朝廷的大官。那时他公务繁忙,很少回来陪我和母亲,每次回来他都会考教我的学业,一旦背不上来那些诗词,他就会用戒尺打我手心。除了学业他还给我请了很多老师,有书画老师,有古琴老师,有舞蹈老师。”
“这么多老师啊?我老家在一个偏远的村里,想请一个识字先生都难。我小时候最喜欢下河摸鱼抓蟹,我娘怕我涨水被淹死,总是拿着柳枝条在河边等我上岸抽我。”
“我在学那些先生教的东西时,脑子里想的全是院墙外是什么样的世界。”秋云淡淡地说。
“后来呢?”
“有一次我被先生责罚打了手心,痛得我午睡时睡不着,我一个人悄悄跑出了院子。”秋云顿了顿,“那是我第一次逃离,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“那你还是蛮勇敢的。”风间夸奖道。
“表面上是,”秋云纠正道,“可真正逃离了那片院墙,我也不敢离家太远。在院墙里面时总是羡慕那群孩子,可以在外面嬉戏玩耍,可真正到了外面,我根本无处可去,陌生的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,路上的陌生人看我的眼神也都很奇怪。我就坐在离家不远的地方,一个人荡着秋千,摇着父亲给我买的拨浪鼓。”
“我小时候都没有玩具的。”
“我玩具还挺多的,都是我父亲给我买的。我把拨浪鼓想象成能实现愿望的法宝,只要我摇得够快,愿望就会实现,我就使劲地摇它,越摇越快,越摇越响......直到那两根绷着的线断裂,珠子崩到了我的额头上,痛得我哇哇大哭。”秋云声音低落,“其实我那时的愿望是想父亲回来陪陪我,可拨浪鼓坏了,我的愿望也就成真不了了。”
“还有呢?”风间觉得秋云还有很多话想说。
“府里的人发现我不见了,发了疯的到处找我。我就坐在秋千上,看着他们在街道上大声喊着我的名字,其实那个秋千离家很近的,只是没人相信,我跑出来就是在离家那么近的地方荡秋千,所以他们没有到那个地方找我。最后我觉得无聊了,主动走到了他们面前,他们一个个高兴得要哭出来。”
“那种情况我也会喜极而泣。”
“那天因为我失踪的消息传到了我父亲那里,父亲破天荒地放下事务,回到家见到了刚被找到的我,用戒尺狠狠打了我手心。”秋云说的专注,“父亲打我时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哭,我笑了出来,我越笑就被打的越狠,于是我就边哭边笑,把父亲都逗笑了。我笑是因为我的愿望实现了。”
“你父亲其实对你还是蛮关心的。”风间说。
风间试着换成秋云的身份,从小接受各种教育,不能随便出去玩,不及格就会挨板子,一个人孤零零的,想着是有点悲伤。
“后来有一天,父亲被奸相杨国忠陷害,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。”
风间的心里忽然一空,呆呆地看着秋云。真是悲伤的氛围,凝结了周围的空气,让人压抑得不舒服。它想上去拥抱秋云安慰她,但他不敢,因为他看不见秋云的表情。
“父亲不在了,再也没有人让我读书练字学画弹琴跳舞了,再也没有人打我板子了。按理来说我应该要高兴的,所有的枷锁都没了,我自由了,没人能管我了。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,我的拨浪鼓坏了,我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。”
风间看见有一道晶莹的泪从秋云眼角流出。
“让风郎见笑了,”秋云不动声色地擦去那滴泪,“这些事情我从来没跟人说过。”
“没事的,”风间安慰道,“一切都过去了......”
“风郎你有没有什么愿望?”秋云问。
“赚大钱,当大官。”
“那要赚多少的钱才算够,当多大的官才算大?”秋云摇摇头,“人心的欲望总是越来越大,越来越难满足,不如说一个小点的愿望吧,最好能容易实现的,就像小孩柜子上的糖,站着够不到,垫垫脚就能摸到。”
“容易实现点的愿望?”风间抓抓头,“那就在乡下有一间房子和一块地吧。房子是最好能在靠近一条小溪的地方,每天种点地保证自己不被饿死,种完地搬一张藤椅躺在小溪边,吹着风,还可以钓鱼,阳光照在溪面上波光粼粼的,再喝杯自己酿的米酒就更满足了。”
“可是夏天在小溪边不会蚊虫太多吗?”
“这个倒是没考虑到。不过这样说的话也就春秋合适了,冬天寒风嗖嗖的,得冻出老寒腿。”
“这就是你想过的生活吗?”
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,老家有一个老头,他家就住在小溪边,他还有一根很长的钓鱼竿,无论什么季节,他都是躺在溪边钓鱼,他还会自己酿米酒,那米酒我趁他睡着喝过,一辈子忘不了那种感觉,美极了。有时候是真的羡慕那个老头。”
“你的性子有点懒散。”
“从小就是这样,能坐着从不站着,能躺着绝不坐着,但参军后就好了。”
“你小时候应该是那种总爱东想西想的小孩,一个人望着天,能看云的变化好久好久。”
喜欢东想西想......性子懒散......风间心里动了动,秋云似乎说对了他。
“我有时候也喜欢听风吹着树叶簌簌的响......”风间小声说。
“有机会的话,我也想过一下你的日子,躺在溪边,听风看云。”
杜预萧梁两人突然走了进来,似乎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。
“回去吧,明天有空再来,天黑了什么都找不到。”杜预说。
风间伸手将秋云拉起,她的手柔软而冰凉。
他凝视着她的眼睛,一如既往的漂亮,可上面似乎有一层雾,他读不懂她的内心。这一刻他离她很近,能清楚地闻到那些脂粉香气,却又相隔甚远。
他想到了秋云的话,你小时候是不是一个总爱东想西想的小孩,一个人看着天,能看云的变化好久好久。
他又想到了萧梁的话,算啦兄弟,这长安城有一百零八个坊市,就算每个坊市只有一个姑娘,你也有一百零八个姑娘,可以选一个去喜欢去爱。你这样纠缠下去,最终的结果就是像他们两人一样互相不得善终。
“我们走吧。”秋云放开了风间的手,很自然。
风间手上还残留着她的温度,此刻他们又远离了。
天已经黑了,街道两旁点着些许灯笼,马车载着四人走了,车轮好久没上过油了,一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风间把头搭在车窗看着窗外的街景,嘴里哼着清冷的调子。
风间走进将军的军营,把有着莲花图案的令牌放在他桌上。
将军拿着一封密信在看着什么,也不抬头看他:“有什么线索?”
“现场大部分东西都被烧毁了,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。”
将军看完密信再抬头看了眼桌上的东西,若有所思:“果然是白莲社。”
“白莲社是什么?”
“是一个邪教组织,这个你暂时管不着。东西放这,人滚吧。”
风间掀开门帘,正准备出去时回头:“将军,你有空的话还是休息一下吧,你的两个女人都很想你。”
“你要管我?”将军看着风间眼露寒光。
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风间一缩脖子,扭头一溜烟跑开了。
军营外的街道上,橘黄的灯笼挂在两侧,不时有寒风吹过,灯笼晃晃悠悠像麦田起伏的麦浪。
风间像一只迷途幽灵,跟着灯笼散发的光辉指引,一路走到了晋昌坊。坊门外有两只威武的石狮,专门阻挡各种邪祟入侵,一只石狮的阴影下靠着月玲单薄的身影。她快要睡着了,双手抱着蜷曲的双腿,靠着石狮的脑袋不时上下晃悠,一缕头发从耳根耷拉下来,在轻风中轻轻摇晃。
风间心里一动,这么晚了月玲在等着谁?还是她只是单纯的贪玩忘了回家。
风间走上前去,盯着月玲的侧脸瞧了会,有点脏脏的,他用衣袖擦去那些灰尘,那张小脸立刻显得娇嫩起来。
月玲缓缓睁开眼,看见面前之人后缓缓地无声地笑了,她伸出双手似乎要风间拥抱她,风间会错了意,伸出双手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说:“回家睡吧,地上冷。”
这时风间偏过头,听见远处的戏楼上隐约有歌声飘来:
“人生只似风前絮
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”